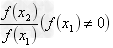我很惊讶,我不是她家的钻石级客户,几乎是葛朗台式的,也不美,土肥圆,不像是个标准的托儿。再说,我普通话还很烂。不过贾平凹说:“只有普通人,才说普通话。”而且女老板坚持让我去,觉得我眼睛亮,看得见明晃晃美丽背后的暗苦。
今年经济不够友好,我那些自称“内心像有地球引力”的创业朋友,艰难地撑着。没想到这个草根女老板会“逆市”开第三家店,似乎中美贸易战、GDP增速有没有6%,那些大叙述都与她无关。
这些年,我们见惯了浮躁,炒房炒币炒鞋,也听了些“爆雷”跑路。大家生怕错了风口,没有风口也要创造风口。大机会时代,大家争做机会主义者,鲜有人做专业主义者。
而这个女老板不太一样。认识她很偶然。我生完孩子8年没进过美容院,第一次“黄着脸”进她家做了护理,第二天脸就肿得像猪头,我像提刀的鲁达,愤怒地冲进镇关西的铺子。
她店的员工都是农村姑娘,来应聘时,土气的、满脸青春痘的、刚离婚的,胖过150斤的,她都收。她招人不看外貌,就一个标准:踏实。她说,每个人都爱美,都会变美。农村队一定会成为仙女队。
她很清楚,农村姑娘的手能释放多大的生产力,正如她自己的。她出身安徽农村,母亲早早离世,一次她在田地打农药中毒,快被毁容了。后来,她来北京闯荡,从最底层的美容师干起。接着,她带村里的一个小妹出来,再带第二个,第三个……
这是她开的第一家店。几年里,我家门口的这条街,店铺开开停停,换脸如翻书。她的店倒成了古董店,老顾客越攒越多。
她像个老派的小作坊主,一副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狂哪吒样儿,不管外面市场风云变幻,豁出命地干活,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儿赚。
在她看来,美容业不是甜蜜的事业,那是苦差事。她管理严,她要求每个员工的手法、滑动的弧度、力道,她的身体就是考试机器。每周末晚上打烊了,每个员工都要在她的脸上、身上考试,她常年浑身淤青。
现在医美漫天飞,喝一杯咖啡的功夫就人变美了,上午植发,下午上班,电梯里充斥着一群无差别美丽女性高喊“整整整,女人美了才完美”的医美广告,无一不在传递着“钱钱钱”。
相比那些热钱,她和几十双手按摩着一寸寸肌肤,慢慢地赚着“冷钱”。她坚持守在这个“实心”行业,她说,习惯了,靠手,人踏实。
天冷了,她要求美容师用温热的牛奶泡手,再去抚摸顾客的脸。中秋了,她从安徽老家托人做土得掉渣、无添加的传统月饼,送给顾客。她不能容忍美容床发出一声咯吱声,老旧了就换。她要求店里的厕所不能有丁点儿臭味,她给厕所放花市买来的香水百合。她给天花板装饰,让客人躺几小时,眼睛不空。
她抠细节,一点儿也不“差不多”。过节,店里用气球装饰,员工吹的大小不一,她一个个扯下来,要求一般大。木地板不平了,她让员工去度假,自己守在店里盯工人装修。一次客人开玩笑说,她家的狗才用这种简陋的吹风机。她听了难受,买了一只近3000元钱的吹风机给客人用。
不到90斤的她“力大无穷”,能扛事。她很像安徽老家那种“能做屋梁也能编小筐”“且柔且强”的竹子。她应付各种检查、各种难缠的客户,店里啃不下的硬骨头都是她的。
阅人无数,练就了她的高情商。都说美容师、理发师是这个世界知道秘密最多的人。她要求她的员工,能聊天,更懂得保守秘密。
日子久了,这里的农村姑娘越来越美,不再“村”,洋气知分寸。有时候看到她会想起小时候安慰矮小的自己的一首诗: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我的孩子长青春痘,有时候放学了自己来美容院清痘,她很喜欢和曾做过幼师的美容师姐姐吐槽作业多,吐槽大人。她说“哪怕忍受清1000个痘痘的疼,也愿意和小姐姐聊天”,这地球懂小孩的大人太少了。她还坚持偷偷给工作不能吃东西的美容师喂辣条。我家的秘密在这个屋子里传播,却也始终没走出这个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