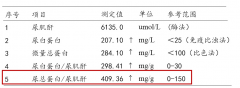大家都知道,对“折中理论”(例如由马歇尔提出的)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新近提出的。该批评认为,折中理论没能认识到均衡的真正内涵。折中理论假设,现实条件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会达到那个状态。这个假设遭到了批评。实际情况恰好相反。这里的情况和我们业已讨论的人口颇有相通之处,但更为突出,也更重要。在某个社会里,如果某一时刻有新的投资发生,资本化率就是将现货转化成未来收入的比率。
它是新增投资的“生产力”比率,是以下两种收入的比率:一、有待形成的资本品的年度价值收入;二、为创造该资本品所放弃的现货价值收入。
资本品数量的变化,只可能源于以下两种途径:要么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相互转化,要么是现存资本因维护不善而逐渐减少。储蓄和消费心理不会对即时利率产生显着的影响。在短期内,资本品的供给不是利率的函数,而是既成的事实。
心理变化会使人们的储蓄(或消费)多少有些变化。但是,与整个社会的资本品供需总量相比,这种影响微不足道。时间偏好比率决定了新资本积累的比率,并影响着未来的而不是当前的利率。由于储蓄有可能转化成投资,这促使个人将他的时间偏好比率向现行的生产力比率看齐。通过稍微增加个人的储蓄或者消费已经储蓄的资本,他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。
就算我们假设其他所有的条件都保持不变,在任何时候,对均衡调整所必需的时间也是难以确定的。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各个时期,只要社会条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(包括人们的心理、道德观念,特别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),利率一直高于均衡水平。
资本稳定而快速地积累的事实,足以证明上述结论。假设对资本的需求以及其他情况保持不变,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达到平衡,取决于以下诸项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人们决定是否储蓄的比率。这一比率是人们参考实际利率和均衡利率之间的偏差(这里还要补上收入增加和储蓄心理成本减少两种情况的调整)而自主决定的利率。
第二项因素是,将新增资本应用于社会现存其他生产要素时,回报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速度有多快。从历史上看,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沧海桑田,绝对不能称得上保持不变。人口的增长、新兴自然资源的发现,这些都加快了对资本的需求。当此巨变,利率反而保持稳定。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我们需要注意,技术进步通常倾向于使劳动和土地更加经济,并增加对资本的需求。
我们所能明确表达的均衡条件,产生这些条件的诸多事件的演变路径或者耗费的时间,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可能是纯理论的,而且是徒劳无功的。我们完全没有执着于相信一定会有一条路径能够达到均衡。这一路径是否存在不会对理论本身的以及实用价值造成任何损害。这一点不言而喻。
如果洞察到人性的本质,我们可以知道,如果某人没被赋予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,却要对后者行动的回报做出明确的保证,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,也是有悖常理的。另一方面,后一类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,他也不会接受前一类人的指挥。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所谓的“双重契约”,在历史上,它以规避高利贷法而着称。良好的判断一定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判断抱有信心,否则整个系统将会陷于瘫痪。也就是说,无论对于自己的判断,还是对于他人的判断,无论是判断的种类,还是判断的程度,判断正确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失误的次数。
上述之多重专业化功能产生的结果,就是企业和薪酬体系,它们是不确定性的直接产物。在剩下的研究中,我们的任务是考察这个现象,深入分析该现象的诸般形态,以及该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及社会组织的诸般关系。企业这个形式既非不可或缺,也非不可避免,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。但是,在特定条件下,企业所具有的特定的优势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。承担经济生活的指挥责任,对这样的功能实施专业化,这就是企业的本质。企业的另一特征是,责任和控制这两大要素不可分离,这一点经常被我们所忽略。在企业制度下,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,他们指挥着社会的经济行为。
上述分析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率,而是资本化比率或交换比率。这里的交换比率指的是现期消费品和财产收入之间的交换比率,也是相对于其他投资机会的投资生产力比率。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里,为获取利息而出借资本,这个现象是否存在,我们还不太确定。作为一种机制或工具,贷款能够将生产要素价值的所有权和实物的所有权进行分离。做出这种分离的动机是,未来的变化会导致要素价值的不确定。就算这不是唯一的动机,也应该是主要的动机。
要素使用者有两种方式获得要素,一是通过租赁;二是通过贷款购买。如果要素的价值保持不变,或者价值的变化可以预测,不管用哪种方式都不会对要素价格产生任何影响,贷款合约和租赁合约可以相互替代。生产者借入资金,进行投资并转化成资本品。他投资的方式是,提前支付给劳动者、地主和资本家,以获得他们提供的资源。
资本的初始所有者究竟是自己投资,还是出租生产要素,或是发放贷款,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未来可以完全预知,投资将没有任何成本。不过,投资显然需要投入最起码的关注和辛劳。这使得投资毕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,而不同于简单提供资本。如果是这样,贷款和严格意义上的利息将会应运而生,采用的利率就是刚刚讨论的资本化或生产力比率(如果投资成本不能忽略不计,还要将它扣除掉)。
投资一经完成,投资收益就仅仅是资本品获得收入的问题。资本要素价值的计算方法是,将这种收入按现行利率进行资本化处理,现行利率由自由资本的市场决定。因为资本品能够大规模地再生产,它的价值不会与生产成本存在明显的偏差。
针对资本品的需求变化,资本品的供给做出适应的调整要耗费一段时间。对于不同的资本品,耗费的时间各有差异。如果某种要素完全不能通过投资再生产出来,它符合古典经济学对土地的描述。笔者的观点是,这类要素在实践中可以忽略不计。
这是因为,从长期看,土地与其他资本品并无二致。对资源勘探和开发做出的投资,和在其他领域的投资相互竞争,与其他投资的生产成本在主要方面基本相似。将资本品供给按照有无弹性以及收入的特殊类别(马歇尔的“准地租”)进行划分,这么做都只是权宜之计。只要没有不确定性,这种分类都无关紧要。
根据发展因素清单,我们还要简略讨论剩下的内容。在静态条件下,我们假设这些因素保持不变。第四项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布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影响个人能力(劳动)的条件和影响资产的条件完全一样。这些条件都完全依赖于社会制度。
我们认为,获得收入的能力要么来自的财产,要么来自遗传。这样的判断来自我们的习惯。个人拿出现有的收入进行投资,开发出新的生产能力,不管这种生产能力是固化在他自己身上,或者凝结在资本品上,抑或是发现、开发出了自然资源,他并不必然应该获得这种生产能力的完全所有权(近乎没有限制的控制权,再加上全部的收益权)。
对于继承财产和遗传能力这两类情况,我们的态度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。对于遗传的个人能力,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它认可为产权;而对于继承物质产品形成的收入,我们却将之贬斥为“不劳而获”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对待,我们很难解释得通。社会需要不断鼓励开发各种生产能力,也要鼓励对这些生产能力认真而有益的使用(社会需要认识到,家庭关系能够确保资产一代一代的连续使用)。
针对获得遗产的权利,还可以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。不过,这些办法是否奏效,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。值得关注的是,社会正在加快限制产权(支配权和收益权两方面)的步伐。这导致在使用私有产权时束手束脚,依个人意愿工作的条件也被层层设限,大量的收入也借“社会”目标的名义被横征暴敛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